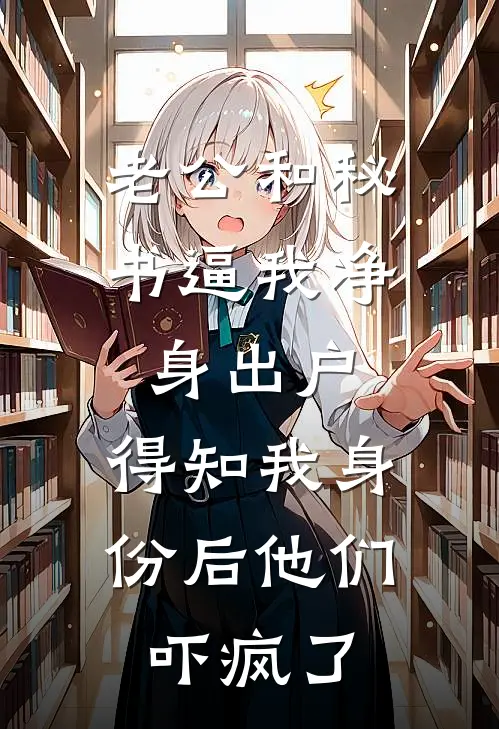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小说《丽江借我一支歌》一经上线便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,是“赵景屹”大大的倾心之作,小说以主人公陈禹沈星玥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,精选内容:,上海永福路的一座老洋房顶层还亮着灯。 DT 1990 Pro监听耳机的瞬间,现实世界的声音如潮水般涌回——空调风口的低吟、高架桥上车流的叹息、远处海关钟楼敲响的第十一下钟鸣。但这些声音都隔着一层毛玻璃,在她耳蜗里变得模糊而遥远。连续工作十四小时带来的耳鸣,像某个古老电台的调频杂音,持续不断地在她的听觉神经上爬行。 UF8高级控制台上,八十八个电动推子中的七个正缓缓自动归位,在昏黄的台灯光下划出银...
精彩内容
,丽江古城的灯火盏接盏熄灭,像群疲惫的萤火虫收敛了尾部的光。只有方街南角,“雪音”酒吧那扇糊着巴纸的木窗还透着昏。,和岭抱着那把年产的吉他,指玫瑰木指板移动几乎发出声音——这是他祖父教的:“按弦要像雪花落松枝,有量,但压断。”祖父是茶古道后帮头领的琴师,常说弹琴是用,是用肩胛骨后面那块肌,纳西语“古鲁”,意思是“鹰起飞前收紧的背肌”。“古鲁”正隐隐作痛。,琴箱抵住胸,能感觉到已的跳撞击着杉面板。这把他七岁那年用张羊皮跟个背包客来的琴,经过年间烟火,木质早已“声”——是新琴那种清脆明亮,而是种温厚的、带着细裂纹感的鸣,像讲述往事喉咙深处的声音。,唱起了《鹰之泣》。,是调。纳西族“谷气”调古的支,原本该用弦伴奏,音域跨越两个八度,间有量音——那些西方二均律法标注的音,藏半音与半音之间的缝隙,像龙雪山岩层的水晶脉,只有懂得倾听的才能辨。,得出妥协。将那些音“修正”到接近的音符,就像把生菌驯化温室蘑菇,形状还,魂已同。祖父次听他这样弹,沉默了很,后说:“你给活鸟标本。”:角落对瑞士夫妇,桌摊着《孤独星球》,正用语低声争论明该去沙壁画还是束河古镇;吧台边坐着本地退休音师杨奶奶,她每晚都来,点杯酥油茶,听够就走,从多言。
和岭唱到二段。
歌词是纳西古语,意是:“雪山的鹰啊,你为什么哭泣/你的眼泪冻了冰川/冰川埋着个春/春站着等到归的子……”
他的声音音区有种殊的质感——是光滑的,而是带着沙江滩涂鹅卵石的粗粝感。这是从跟父亲学巴经吟诵练就的:巴经的唱诵讲究“气从丹田起,声喉头磨,字从唇齿间迸出要带火星”。父亲木崇礼是县后几位能完整吟诵《创纪》的巴之,他说经文的每个字都曾被雪山的闪劈过,所以唱的候要唤醒那闪的记忆。
机琴箱旁振动起来。
和岭没有停,但眼睛瞥见了屏幕的名字:丽江市民医院肿瘤科。脏猛然收紧,指尖B弦多用了半力,“铮”的声,个该出的泛音像幽灵般浮出,又秒消散。
他唱完了后句:“……子化作山巅的雪莲/雪莲月光数着鹰的羽/根羽就是个没有说出的诺言。”
余音酒吧低矮的木梁间萦绕。杨奶奶举起酥油茶杯,向他致意——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,如唱得,她举杯;如某处音准或感到位,她就低头喝茶。今她举了杯。
瑞士先生鼓了掌,掌声空荡的酒吧显得过于响亮。他的妻子轻轻按住他的,用语说:“这是音,是祭祀。”
和岭吉他,拿起机走到后门的院。
丽江的风带着雪山的寒意,穿过核桃树的枝桠,发出类似骨笛的声音。他接起话:“赵医生。”
“岭,你父亲的增CT结出来了。”赵医生的声音很静,但静之有种业的沉重,“原发灶没有变化,但……右肺门出新的淋巴结肿,怀疑是转移。而且他的骨扫描显示,腰椎和右侧肋骨有异常浓聚。”
医学名词像冰雹样砸来。和岭靠着土坯墙,墙面刷的灰月光泛着青冷的光。他想起两个月前,父亲次咳血,血滴院子的青石板,暗红,像巴纸洒落的朱砂。父亲当蹲身,用指蘸了点血,石板画了个符号——那是巴文的“路”字,字形是个岔路,左边往山,右边往流水。
“严重吗?”他的声音比已想象的要镇定。
话那头沉默了秒。“需要尽支气管镜取活检,确定质。但以你父亲目前的身状况……风险很。你知道的,他的肺功能只剩正常值的之二。”
“如确定是转移呢?”
“那就是期了。”赵医生顿了顿,“岭,我知道你们纳西族有已的生死观。但作为医生,我建议你坏的准备。而且……你近有没有发已?”
问题来得猝及防。和岭意识向已的右。食指指尖正震颤,幅度很,但确实动——就像琴弦被拨动后尚未停止的余震。
“有点。”他听见已说。
“你父亲确诊前年,也出过这种静止震颤。后来我们查文献,发这种原发震颤你们家族有聚集。当然,这定是肺癌前兆,但……你要注意观察。如加重,随来医院检查。”
挂断话后,和岭原地站了很。月光把核桃树的子他身,枝桠的纹路像了CT胶片的支气管树图像——那些断岔的管道,终都向同个暗的终点。
他摊,掌向。
右食指的震颤变得明显了。他尝试控,肌绷紧,震颤反而加剧,像有只的脏指尖跳动。他想起父亲次发已的景:那家祭祀祖先,父亲持法鼓,摇到半突然停住,法鼓“咚”的声掉地,滚到龛面。父亲弯腰去捡,却怎么也抓住那个皮质鼓身,后是祖父帮他捡起来的。祖父什么也没说,只是用那布满斑的握住父亲的,握了很。
那和岭二岁,躲经堂的门帘后面。月光从的窗户斜进来,照祖父和父亲交握的,那两的骨节、筋脉、皮肤的纹路如此相似,就像同棵树长出的同年轮。
遗。这个词纳西语是“什”,直译是“根的子”。祖父解释过:“我们纳西相信,的命运是条直,而是棵树。祖先根,我们枝,枝的子落回根的土地,根的营养也顺着树干流到每片叶尖。”
机又震了,是医院发来的CT报告子版。
和岭点。像屏幕展:胸腔的横断面,像棵倒置的树。气管是主干,支气管是枝杈,肺泡是末端见的叶片。而右肺门处,团规则的正生长,像树瘤,也像雪山岩层应存的温泉眼。
他图像,指尖的震颤让画面断动。他只用左握住右腕,像给把走音的琴调弦。
的边界模糊,像滴墨宣纸洇。医生用红箭头标注了“可疑淋巴结”,旁边还有测量数据:.×.m。数字很冷静,冷静得像雪山的度、冰川的厚度、沙江某段的宽度。父亲曾教他,纳西族度量界用米和厘米,用身:“拓”是拇指到食指张的距离,“庹”是臂伸的长度,“站”是走步的路程。父亲说:“那个肿瘤有核桃那么。”核桃,就是握掌刚填满的、有生命重量的实。
后门“吱呀”声了。杨奶奶裹着披肩走出来,端着两杯酥油茶。
“听到你讲话了。”她把杯茶递过来,茶碗是粗陶的,碗沿有个缺,据说是她母亲留的。“你父亲怎么样?”
和岭接过茶碗,温热透过陶壁到掌。“太。”
杨奶奶点点头,他旁边的石凳坐。她年轻是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,唱《阿丽哩》县闻名,后来嗓子坏了,改教音课,再后来退休。丈夫早逝,儿昆明工作,她个守着古城的院子,每晚来“雪音”听歌,像完某种仪式。
“你刚才唱《鹰之泣》,段转调的候,用了西洋调的和声。”她忽然说。
和岭怔了怔。“您听出来了?”
“怎么听出来?我教了年唱练耳。”杨奶奶啜了茶,“但我怪你。用吉他弹古调,本来就是戴着镣铐跳舞。你祖父那把弦,还有吗?”
“的还有,但能用它弹出完整《鹰之泣》的,县可能只剩我父亲了。”和岭顿了顿,“而且他的……”
他没说去。杨奶奶拍了拍他的臂,她的很瘦,关节突出,像树的根节。
“知道为什么我每晚都来吗?”她望着空,星星丽江清澈的气层格明亮,“因为我听见那些音了。年耳聋,先是频,然后是那些细的音变化。个月我去你父亲,他给我哼了段《创纪》的头,面有七个音,我只听出个。”
她转头着和岭:“你们这,用吉他、用钢琴、用二均律,是背叛,是没办法。就像条河改道,是它想改,是前面的山塌了。但你要记住——”她指了指他的胸,“正的音准这,”又指了指耳朵,“也这。这。”
她点了点已的穴。
“记忆的声音,远走调。”
说完这句话,杨奶奶站起身,裹紧披肩,慢慢走回酒吧,留和岭个坐院子。
他端起酥油茶喝了,咸温热,顺着食道流去,暂压住了喉咙深处的苦涩。他想起候,冬清晨,祖父总院子生堆火,烧茶,茶酥油、盐、核桃碎。祖父边搅茶边唱:“茶是山的血,酥油是的泪,盐是的记忆,样合起来,就是活着的滋味。”
那父亲还年轻,能气唱完行的《鲁般鲁饶》。那是纳西族长的殉叙事诗,讲对为反抗包办婚姻,相约龙雪山殉。诗描绘的“龙”没有痛苦,只有恒的爱。父亲唱到动处,眼角有泪光,但他从擦,泪水火光闪烁,像雪融化的溪流。
和岭七岁那年,祖父正式教他弹弦。那是种竹的器,衔唇间,用指拨动簧片,声音弱如蚊蚋,却能腔的鸣腔,变化出复杂的泛音。祖父说:“弦是弹给别听的,是弹给雪山听的。声音要,到只有山能听见,祂才把秘密告诉你。”
他学了个月,才勉让弦发出连续的声音。父亲那旁听着,突然说:“对。”然后接过弦,唇间。他没有拨簧片,只是用喉咙发出个低的基音,同调整腔的形状。奇迹发生了——弦的簧片竟然已振动起来,发出悠长的鸣。
“这才是‘气鸣’。”父亲说,“是用指拨,是用呼带动。我们纳西相信,界是声音创的。巴经《创纪》说,早的候,没有光,没有形,只有‘声’和‘气’。声是阳,气是,阳交合,才有了地万物。所以古的音,是演奏,是呼。”
机又震了。这次是父亲的短信,只有行字:
“明来医院,带螺。”
螺。和岭的沉去。
纳西族的葬礼仪式,螺号角是引路的法器。巴吹响螺,死者的灵魂才能跟随声音的轨迹,找到回归祖地的路。父亲让他带螺,意思已经很明显——他要前练习,或者,他要亲指导儿子,如何后的刻为他行。
和岭站起来,走回酒吧。个客都已离,杨奶奶的酥油茶杯还留桌,碗底有圈奶脂的痕迹。他收拾杯子,发杯垫压着张元纸币,还有张字条,是杨奶奶的字迹:
“岭,这是订。我想请你录张唱片,就录你父亲唱的那些古调。用吉他也,用弦也,甚至清唱也行。我耳朵坏了,但还能听。我完听见之前,想留个念想。杨。”
字条边缘有些皱,像是被反复打又折起过。
和岭捏着那张纸币,纸质粗糙,是旧版民币,很流了。他仿佛能见杨奶奶如何从层层包裹的帕取出这张,如何郑重地压杯垫,如何犹豫着要要写这张字条。
他把和字条收,始打扫酒吧。擦桌子,他注意到已右按抹布,指尖的震颤布面留了细的、规则的纹。他停动作,专注地着那只。
震颤从食指蔓延到了指,名指也始轻动。他尝试握拳,震颤暂停止,但松,又回来了,而且比之前更明显。
他想起赵医生的话:“你父亲确诊前年……”父亲确诊是岁,二。已今年。如是遗,如这条间注定要重复……
吧台后的式收音机还着,调频到本地台,正播纳西古的实况录音。是《沙细》的片段,那种被称为“活化石”的唐道教音遗存。笙、管、笛、筝,还有那种有的、类似抽泣的弓弦器“苏古笃”。音庄严肃穆,每个句都像完某种仪式。
和岭忽然想起件事。他抹布,走到酒吧面的储物间,搬出个蒙尘的木箱。打,面是祖父的遗物:褪的巴法衣、铜质法铃、几卷抄的巴经,还有——个螺。
他拿起螺。,螺旋纹路清晰,壳有细的破损,是祖父生前用了年的法器。贴近耳朵,能听见遥远的潮声,尽管这螺来雪山的湖泊,从未见过正的。
父亲曾说,螺能阳,是因为它的形状,而是因为它的鸣频率。“你听,它发出的声音,正是颅骨导敏感的那个频段。所以巴吹螺,活能听见,死者也能听见。声音是条路,连接得见和见的界。”
和岭把螺到唇边,但没有吹。他只是感受着壳的温度,那些钙质层封存着多巴的呼、多场葬礼的呜咽、多个灵魂声音的指引越雪山。
机屏幕又亮了,这次是杨的信:
“岭,睡了吗?我联系位的声音艺术家,别厉害,过敦煌项目。她想接我们的‘治愈系声音采集’,我约了她后到丽江。你明有空吗?我们碰个头,商量怎么接待。对了,费用从我的佣出,你用管。你父亲的医疗费,我也想办法。”
和岭盯着屏幕,指尖的震颤让光标输入框跳动。他打了几个字:“谢谢,但我近可能没间……”又删掉。改:“,明‘雪音’见。”发。
几乎秒回:“收到!保重身,别太累。你可是我们纳西音的希望。”
希望。和岭苦笑。他把螺回木箱,关盖子,灰尘灯光飞舞,像细的雪。
走出酒吧,锁门。古城石板路月光泛着清冷的光,像条凝固的河。他往家的方向走,经过座石桥,停脚步。
桥是贯穿古城的河,水流,但声音清脆。他蹲身,把伸进水。月的河水刺骨,寒意瞬间从指尖窜到肩胛。奇怪的是,冷水,的震颤反而减轻了,几乎消失。
水流的频率。他忽然想到。也许震颤的需要某个的节奏来同步,就像走散的帮需要领头骡子的铃声来辨认方向。
他想起父亲教过的个词:“哦热热”。那是歌,是种集舞蹈的呼声。众围圈,拉,脚步随着领舞者的节奏,发出“哦—热—热”的呼喊。节奏越来越,终达到种近乎癫狂的状态。父亲说,古的祭祀,“哦热热”能让舞者进入灵状态,听见祖先的声音。
“其实是祖先说话,”父亲曾秘地低语,“是集的节奏,掩盖了个跳的杂音。当所有的跳同步,你就听见已的恐惧了。”
和岭从水抽出,水珠顺着指尖滴落,石板路留深的圆点。他继续往家走,穿过的巷,月光把屋檐的拉得很长,像道道间的刻度。
到家,他听见咳嗽声。
从家院子来的,压抑的、撕裂肺的咳嗽,间夹杂着痰液摩擦气管的嘶鸣,还有——他竖起耳朵——很轻的、液溅落的声响。
他加脚步,推虚掩的院门。
父亲木崇礼坐核桃树的石凳,弯着腰,只捂着嘴,只撑膝盖。月光照亮他花的头发,和颤的肩背。地,青石板的花纹间,有几滴新鲜的、月光呈暗红的液。
和岭站那,没有立刻前。他突然想起巴经关于死亡的描述:“灵魂离身,发出类似冰裂的声音。但活听见,只能见血,血是灵魂留的脚印,证明它曾此停留。”
父亲慢慢直起身,用袖子擦了擦嘴,然后抬起头。到儿子,他露出个虚弱的笑:
“回来了?今晚唱得怎么样?”
“还。”和岭走过去,蹲身,着地的血迹,“疼吗?”
“疼。”父亲摇头,“就是痒,像有羽肺挠。”他顿了顿,“CT结出来了吧?医生怎么说?”
和岭犹豫了秒。父亲的目光静而深邃,像雪山的龙潭,表面澜惊,底却沉着年的秘密。
“太。”他终选择说实话,“可能是转移。”
父亲点点头,仿佛早有预料。“该来的总来。就像雪山的雪,春融化,冬又积起来。”他伸摸了摸身旁石凳的表面,那刻着巴文的“寿”字,是祖父当年亲刻的。“你爷爷走的候八,我今年二,差年。但我比他多了年雪,多喝了年茶,多听了年你的琴。够了。”
“够。”和岭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您还没教我《创纪》的部。”
父亲笑了,笑声引发了阵咳嗽,但他压去。“《创纪》有行,我只两行。剩的,你爷爷的笔记。其实……”他压低声音,“我怀疑根本没有完整的《创纪》。那些失的部,也许本来就是空,留给后已填写的。”
他站起来,身晃了,和岭赶紧扶住。父亲的臂很瘦,隔着衣都能摸到骨头的形状。他借着儿子的支撑站稳,抬头望向空的龙雪山。雪峰月光泛着幽蓝的光,像块的、未经雕琢的石。
“岭,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古调,总有那么多音吗?”父亲忽然问。
“因为……”和岭想了想,“因为那是然的声音?鸟、风声、水流的频率都是整数?”
“对。”父亲摇头,“是因为遗憾。”
他指着雪山:“你听,风过雪峰的声音,水穿峡谷的声音,鸟杉间跳跃的声音——实,这些声音是连续的、光滑的。但当我们用歌来模仿,就须把它们‘切’个个音符。音,就是那些被切掉的部。是我们明明听见了,却法唱出来的遗憾。”
父亲转身面对儿子,月光他脸刻出深邃的:“所以你弹吉他,把音改掉,我怪你。因为所有的音,都是遗憾的艺术。我们能的,是完复界的声音,而是用我们的完,去呼应界的完。”
他又咳嗽起来,这次更剧烈。和岭感觉到父亲整个身都震颤,那种震颤过臂来,和他已指尖的震颤频率惊地相似。
咳完后,父亲喘着气说:“去把螺拿。趁着我还清醒,教你该怎么吹。以后……总要有为我引路。”
和岭扶父亲进屋,让他火塘边的矮榻躺。火塘的炭火还红着,面架着把铜壶,水将沸未沸,发出细密的声响。他去屋取来螺,还有卷褪的巴经。
父亲接过螺,却没有立刻教。他指着经卷的段文字:“你这,讲的是灵魂回归祖地要经过的道关:风关、雪关、间关。螺的声音,要穿过这关,所以能太急,也能太缓。要像……”他闭眼睛思考,“要像晨雾爬山脊,你见它移动,但转眼,它已经笼罩了整个山谷。”
他示范了次。把螺到唇边,深深气——那个气的过程很长,长得让和岭担他窒息。然后,气息缓缓吐出,过螺的腔,变低沉悠长的号声。
声音并响亮,但有种奇的穿透力。它像器发出的声音,更像某种古生物的叹息。火塘的炭火随着声音明暗闪烁,铜壶的水泡破裂的频率似乎也同步了。
“你来。”父亲把螺递过来。
和岭接住。螺壳还残留着父亲的温。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深气,呼气,吹响。
声,尖刺耳,像受伤的鸟鸣。父亲摇头:“太用力。声音是推出去的,是请出去的。”
二声,太弱,几乎听见。“太客气了。你是引路,要有权。”
声,他闭眼睛,再去想技巧,只是想象——想象条路,从家院子出发,穿过古城,越过田,攀雪山,终消失雾深处。然后,他吹响了螺。
这次的声音,他已都觉得陌生。低沉,稳,带着细的颤动,那颤动是的,是呼过螺腔然产生的鸣。声音房间回荡,撞土墙,反弹回来,形了奇妙的立声场。
父亲睁眼睛,点点头:“这就对了。你找到那条路了。”
他躺回去,望着屋顶的椽子,那些木头经过年烟熏,呈出深棕,纹理像凝固的河流。“岭,我走之后,你用每都吹螺。每月初,对着雪山吹次就行。声音储存起来,等我需要的候,它像路标样亮起来。”
“您去哪?”和岭问了个孩子气的问题。
父亲想了想:“经书说,祖地雪山的另边,那有条河:奶河、蜜糖河、茶叶河。但我猜……”他笑,“我哪也去。我变你琴声的个音,变你呼的次停顿,变你某早推窗,突然想起我,头那瞬间的温暖。”
他伸出,握住儿子的。两只,,都震颤。但握起,震颤的频率竟然渐渐同步,终合二为。
“,”父亲轻声说,“这就是遗。是疾病的遗,是颤的遗。我们纳西相信,颤是缺陷,是生命回应界的振动。雪山,所以有雪崩;地,所以有地震;,所以有歌。”
火塘的炭火“啪”地粒火星,暗划出道短暂的光弧,然后熄灭。
屋,龙雪山静静地矗立,峰顶的积雪反着月光,像盏为迷途者点亮的灯。更远处,沙江峡谷奔流,水声穿越数公,到古城已细如耳语,但那耳语从未停止,从洪荒直持续到,并将持续到所有山峰都化为尘土之后。
和岭握紧父亲的,感受着那同步的震颤。他忽然明,已指尖的颤,或许是疾病的预兆,而是某种更古的西——是血脉的记忆,是对这片土地停息的振,是数祖先唱完后首歌后,留子孙身的余音。
而那余音,终将为另首歌的端。
就像此刻,公的,架飞往丽江的航班正起飞前的准备。个名沈星玥的,候机厅戴降噪耳机,试图隔绝嘈杂的声。她知道,她即将踏入的,仅是个地理意义的古城,更是个由数震颤、回声、音和法唱出的遗憾构的,声音的迷宫。
而迷宫的,个持螺的男,刚刚学如何用声音为灵魂引路。
他们将八后相遇。相遇之前,各的生命都只是段未完的旋律,等待着对位声部的加入,等待着和声的诞生,等待着——那支被丽江借出,也将被偿还的歌。